

研究量子力学三种主要方法
电子说
描述
在1814年出版的《关于概率论的随笔》中,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提出一个假想的生物:它拥有无穷的智慧以至于它知道整个宇宙所处的状态。对于这个后来被称为“拉普拉斯妖“的生物来说,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变成了已知的。因为根据艾萨克.牛顿的理论进行计算的话,过去和将来都由现在完全决定。
拉普拉斯妖并不是可以实现的思想实验(这个想象中的智慧体即使存在的话也会和宇宙一样大)。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初始状态认知的缺失,混沌动力学会放大其造成的影响,从而让预测变得完全不可能。但是,原则上牛顿力学是决定论的。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量子力学改变了一切。往常的物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量子力学同样包含这些内容,同时它还引入了一些新的原则来确定:当系统被观察或测量时会发生什么。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即使是理论上,测量结果也不能完全被预测。我们最多只能根据玻恩规则预测每种结果出现的概率:波函数表示每种测量结果的概率幅,得到每种结果的概率等于相应概率幅的模平方。正是这个特征使得爱因斯坦抱怨上帝投骰子。
科学家一直在寻找解释量子力学最好的方法。有许多有力的说法,它们有时被称为量子理论的“诠释”,另一方面,我们用:一系列可以给出与实验结果相同的预测结果的理论来阐明。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的基本概念都依赖于概率。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概率”?
像很多微妙的概念一样,概率是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的概念,但当我们仔细考察它时就能发现它的微妙之处。你多次抛一枚硬币;它最终是朝上还是朝下是无可预测的,但是如果我们抛很多次,就会发现正面朝上的次数大约占50%,反面朝上的次数也大约占50%,因此我们说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反面朝上的也是50%。
多亏了俄罗斯数学家安德雷·柯尔莫哥洛夫(Andrey Kolmogorov),我们知道了如何处理关于概率的数学问题。概率是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所有独立事件的概率加在一起为1,等等概念。
有很多种方法来定义概率,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类。一类认为概率是“客观的”或者“物理的”,这种观点认为概率是系统的基本性质,是我们理解物理行为的最好方式。这种观点的例子是频率主义(frequentism),它将概率定义为多次实验中某事件发生的频率,就像我们抛硬币实验中做的那样。
另一类是“主观的(subjective)”或“证据的(evidential)”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概率是主观性的,他是一个人关于什么是真或者什么将要发生的主观想法或信仰程度的反映。一个例子是贝叶斯概率(Bayesian probability),它强调了贝叶斯定理(Bayes’law),贝叶斯定理是一个关于我们在接受新的信息后如何更新我们新概率的数学理论。贝叶斯学派认为,理性生物在没有得到完全的信息时会相信他能想到的所有可能性,但他们会根据新获取的信息更新这种可能性。与频率主义相反,在贝叶斯主义中,用概率形容一次独立事件是完全合理的,比如谁将赢得下次大选,甚至是我们不确定的过去发生的事。
有趣的是,理解量子力学的不同方法会涉及关于概率的不同意义。思考关于量子力学的问题有助于对概率的理解,反之亦然。或者,更悲观的是,也许目前关于量子力学的理解并不能帮助我们在各种关于概率的学说中做出选择,因为每种学说都有其相应的关于量子力学的公式。
让我们考虑理解量子力学的三种主要方法。
一种是“动态塌缩(dynamical collapse)”理论,例如1985年由Giancarlo Ghirardi, Alberto Rimini和Tullio Weber提出的GRW模型。
另一种是“导航波(pilot wave)”或“隐变量(hidden variable)”方法,最著名的是David Bohm于1952年根据Louis de Broglie的早期想法提出的德布罗意-玻姆理论。
最后一个是1957年Hugh Everett提出的多世界理论。
每一种方法都表达了一种解决量子力学测量问题的途径。问题在于传统量子力学用波函数描述系统状态,波函数随时间的变化由薛定谔方程决定。至少在系统被测量之前是这样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波函数会在测量时突然塌缩到特定的测量结果上。塌缩的方向是不可预测的。波函数给每一个可能的测量结果分配了一个数字,每一个测量结果出现的概率等于相应的数字的模平方。和测量相关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什么是“测量”?测量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测量和通常的演化不同?
动态塌缩理论或许提供了测量问题的直接解决方法。他们认为量子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内禀的随机性,因为通常粒子会按照薛定谔方程演化但偶尔它们也会出现在一些特定的位置上。这些塌缩非常罕见以至于我们不太可能在在真实的测量中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在大量粒子组成的宏观系统中,塌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说明宏观物体-比如薛定谔的猫-从演化进入可测量的叠加态中。巨大系统内的所有粒子和其他粒子纠缠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个粒子塌缩,其他粒子也会被带上。
随机性在这样的理论中是宇宙中客观存在的基本性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精确的决定未来。动态塌缩理论和古老的频率论者的观点相一致。下一次实验将要发生什么无从得知。我们知道的只是多次实验中每种结果出现的频率。在这种观点中,即便拉普拉斯妖知道了宇宙的完整状态,它也不可能精确的预知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导航波理论把我们带回了经典力学的宇宙,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当我们不进行观测时,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隐变量的实际值。我们可以完全了解一个波函数,但是我们只能通过观察它们来了解隐藏的变量。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承认我们的无知,并引入一个关于它们可能值的概率分布。
导航波理论展示了一幅非常不同的画面。在这个理论中,没有真正的随机性;波函数的演化是完全确定的,就像牛顿力学中的经典状态一样。这个理论中的新内容是关于隐变量的概念,例如粒子的实际位置,这是需要添加到传统波函数上的隐变量。粒子就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那样,波函数只是用来引导粒子的运动。
导航波理论中的概率是主观因素导致的。一个既知道波函数又知道所有隐藏变量的拉普拉斯妖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但一个只知道波函数简略版的小妖只能做出概率预测。
最后是多世界理论,它是我最喜欢的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但它也存在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是概率是如何被引入的。
多世界量子力学的公式是最简单的。它包含遵循薛定谔方程的波函数,这就是全部。其中并没有包含塌缩和附加的变量。我们利用薛定谔方程来预测当我们对一个处于叠加态的量子体系进行测量时会发生什么。观察者和被观察系统形成纠缠在一起的叠加态。组成叠加态的每个分量中的系统部分都有确切的测量值,而测量者可以测量这些值。
Everett的天才想法是“这就足够了”——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叠加态每个分量中的系统演化从其他分量中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波函数的一个分支,或者“世界”。这些世界不是人为引入的,它们蕴含在量子力学的公式中。
关于多世界理论的想法看起来非常激进和难以接受,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中概率的意义是什么。在多世界理论中,我们知道波函数的确切形式,而且它按照确切的方式演化。不存在任何未知性和不可预测性。拉普拉斯妖可以精确预测宇宙的未来。那么概率是怎么回事?
“自定位(self-locating)”或“参数化(indexical)”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解释。想象你将要测量一个量子系统,实际上是让波函数进入不同的世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只可以进入两个世界。)。“测量我将处于哪一个世界?”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将会变成两个人,每个进入其中一个世界,两者都是真正的你。
但是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关于宇宙的完整波函数,依然有些信息是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处于波函数的哪个分支中。从波函数分裂后到观察者测量出他所在分支中力学量的值之间一定存在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个分支。自定位不确定性最早由物理学家Lev Vaidman提出。
你也许会想你可以很快的去观测实验结果,这样就不存在上面提到的那段时间。但在现实世界中,波函数分裂的非常快,至多不多于0.0000000000000000000021秒,因此你总是不能即刻知道自己处于哪一个分支上。
自定位不确定性和导航波理论是关于不确定性的不同看法。你可以知道关于宇宙的一切,但是不确定性(也就是你在宇宙的哪个分支中)仍然存在,你的不确定性遵循通常关于概率的规则,但是,真正要接受这些观点,还要付出一些努力。
你可能会想着现在不进行预测,而是在分裂发生之前进行测量。这样就没有什么不确定的了;你完全知道宇宙将如何演变。但在这一假说中包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所有未来的你将是不确定的,他们应该使用玻恩的规则计算在某一分支中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真正随机的宇宙中,按照玻恩法则给出的各种结果的频率来指导生活是有意义的。(David Deutsch和David Wallace使用决策理论对这一论点进行了严格的论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概率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自定位不确定性的不同版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考虑所有可能世界的集合——一个人所能想象到的所有情况的不同版本。一些这样的世界遵循动态坍缩理论的规则,每一个世界都由所有量子测量的实际结果来区分。其他世界用导航波理论来描述,每一个世界的隐变量都有不同的值。还有一些是多世界的理论起支配作用,其中的观察者不确定他们在波函数的哪个分支上。我们可以认为概率的作用是表达我们个人对这些可能世界中哪个是真实世界的可能程度。
概率的研究把我们从掷硬币带到分支宇宙。希望我们对这一棘手概念的理解将与我们对量子力学本身的理解共同进步。
-
量子力学三大定律公式2024-01-15 10286
-
量子力学的定义是什么 量子力学三大基本原理2023-09-12 18630
-
量子力学经典之固态物理应用2020-08-06 2138
-
量子力学经典量子力学的原子理论应用之空间量化2020-08-04 3286
-
进一步理解量子力学经典 多方面丰富相关图表2020-08-02 2162
-
世界先进的用以量子力学研究的基础设施2020-07-16 2178
-
基于定位与量子力学的设计应用2017-09-19 1465
-
量子力学和物质波2008-11-27 1012
-
量子力学精品课程2008-11-25 648
全部0条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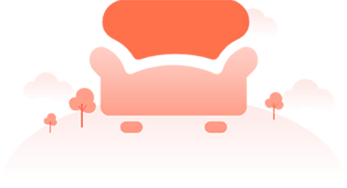
快来发表一下你的评论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