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宁:为什么中国没有像ChatGPT和Vision Pro这样的创新产品?
描述
6 月 10 日,产品战略专家梁宁和图灵联合创始人刘江围绕“ ChatGPT 真需求”主题进行直播对谈。
梁宁,产品战略专家,曾任湖畔大学产品模块学术主任,联想、腾讯高管,CNET集团副总裁。
工作经历横跨 BAT,与美团、头条、京东、小米等企业有长期深度交流 。
结合最近热点,两位老师认为 ChatGPT 和苹果 Vision Pro 代表了信息产品未来的两个方向,从第一性原理——用户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看透表象,抓住其背后的本质。
以下是本次直播的内容节选。
过去的生态位决定了中国是供给驱动
刘江:ChatGPT 和苹果的 Vision Pro 是两个原创性非常大的产品,相比之下国内的原创能力还是稍弱一些,你是怎么看待的?
梁宁:企业和生物一样,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生存。什么叫核心竞争力?就是你在你的生态位上能够活下去。我想到我经历了三代企业家,他们的生态位其实略有变化。
三代企业家指的是三代互联网创业者。
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以柳传志为代表,联想集团创始人,以硬件为主,推动了PC、基础通信技术普及。
第二代互联网创业者:马化腾、李彦宏等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造就“连接”平台。
第三代互联网创业者:王兴、张一鸣等新兴人物赶超原有巨头。
刚才你提问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了 1996 年我在联想的新产品部,工作就是做市场研究,就是看看市场有哪些新产品联想可以代理或者自己开发。
相隔 20 多年的时间再回头看,我比较得意的一件事就是,1996 年我给联想的总裁办做了一次汇报,说互联网就要开始了, Internet 浪潮就要开始。那个时候是1996 年,我们决定要下场,那次汇报的结果是联想决定代理调制解调器。
刘江:对,那就是互联网的起点。调制解调器是不是叫“猫”,那时候我们都说猫。
梁宁:接着到 1997 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实在太小,不值得开一个新的部门来做,于是我们就在新产品部代理了调制解调器。97 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部门的调制解调器营业额占整个中国市场的70%。
从这个起手,你就能够看到当时更多的企业家怎么去做选择。你看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企业家,大家个性都完全不一样,风格也迥异。但是他们是怎么去做选择的?可能我们更容易去选择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确定收益的这一部分的东西。
刘江:那时候联想是多大的一个规模?
梁宁:97 年,联想的电脑第一次登顶。当然那一次我们还是有争议,但是至少有两家统计公司出的数据显示联想电脑是中国市场的第一名。
但是 98 年的时候就没有争议了,联想电脑就是中国市场冠军。1997 年的时候,联想大概卖了 80 万台电脑,同一年长虹卖了 800 万台电视。
刘江:那时候绝对是市场第一。
梁宁:所以隔了 20 多年时间,再回想一下 1996 年的我都在干什么,我会觉得当年的工作其实毫无价值。当时我那种自负,或者是对自我评价过高的心理,纯粹是“没见过世面”。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什么都缺。
我刚才为什么在讲联想卖了 80 万台电脑,长虹卖了 800 万台电视,是因为在 97、98 年的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没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视。更不用说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第一辆汽车,女孩没有自己的第一支口红,98 年我是没有涂过口红的。
刘江:对,1996 年我们中国的人均 GDP 刚刚赶上撒哈拉以南沙漠国家。
梁宁:非常贫困。
刘江:所以那时候,中国实际上是那么一个(很低的)生态站位,是吧?
梁宁: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就是供给不足,什么都缺。
如果大家看过那个时候王朔写的小说,他其实讲了很多大家到处找货源的故事。所以当时的发展是供给驱动,只要能够组织生产,能够组织规模供货,就可以生存。
那个时候联想是不用做用户洞察的,联想主要在讲管理。别人都是小舢板,但是如果能够驾驭一个规模性的共赢、规模性的客服,就是大企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上一批中国的企业都是低端规模,这是因为当时整个中国供给太匮乏了。
之前只要能够用最快的速度,用相对低端的产品,进行组织供给,就可以填平所有用户需要。但突然之间牌子一翻,今天变成了供给过剩。所以我们一方面说经济发展缓慢,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因为中国用户什么都不缺了。
即使是到县城去,大家好像什么也不缺。1982 年的时候,中国 2 亿人口在城镇,我们小时候都学过那句话:10 亿人口,8 亿在农村;2022 年 9 亿人口在城镇。过去 20 年,城镇化不断发展,有 7 亿人搬到城镇,也就是中国建了整个 7 亿人的城市生活配套。
刘江:7 亿人,相当于两个美国的全部人口,差不多是整个欧洲的人口数量。
梁宁:对,这就是我们过去 20 年的情况,所以一切的增长性都来自于此。7 亿人要到城市开展新生活,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的发展其实一直是匮乏驱动和供给驱动。
我讲过如何交付确定性,即如何在不确定中的世界中交付确定。这个词去年成了一个热词,大家都在讲如何在不确定中拥有确定。但实际上我还得自己去破掉它,因为确定性是你应该交付给别人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我们更应该善于驾驭不确定的东西,因为确定性根本就不存在。
尤其是像今天的这个拐点时刻,持续 20 年的创世界的工程结束了,城市化干得差不多了,互联网化干得差不多了,包括华为自己有一句话叫“以前看天花板,现在要看天了”。
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整个中国的原创性能力的问题。说句老实话,这是因为以前我们不需要原创,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匮乏的、供给驱动的、缺东西的状态,那成熟的供给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照着它来就可以了。但是突然之间,有变化了。
刘江:我们人均 GDP 是 1 万多一点,而美国接近 7 万美元,我们才刚刚超过了全球平均值。
梁宁:2020 年,中国宣布我们步入万元美金社会,人均 GDP 过万,这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水平。我当时是觉得非常兴奋的,但忽然之间发现说这是一个地球的平均水平。
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不单纯是中国的玩法变了,整个世界,大家整体创造的水位、财富的水位和创新的水位,全都拉高了,所以还照着原来的那个方式肯定不行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出现像 ChatGPT 或是 Vision Pro 这种创新产品。
像 ChatGPT,它首先是一个工程的创新,它是搭了一万个 GPU 的计算阵列,然后在大模型里有了涌现的能力。他们首先是搭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程,然后往里头放了可运算的数据,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
如果相同的情形放在中国,首先你就会被问: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国内首先考虑的是实用和降本增效
梁宁:国内的土壤目前还没有这种创新的基因。第一是(ChatGPT)这个事情本身,是先干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东西,然后会发生什么、会涌现出什么,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你看 Sam Altman 在智源大会上的演讲,他也在说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它背后的机制,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像这样的一个无关实用主义的、无关既得利益的尝试,可能在很长时间,在咱们“匮乏”的、连温饱都一直都在为此而努力的中国,是很难出现的。其实这本身就不在我们的基因里,就不在我们的这种特性里,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苹果的 Vision Pro,刚才其实我也和刘江老师讨论了,我觉得非常震撼。2014 年 Facebook 的大会发布了一个 VR,从那一版基本上每一代的主流产品我都试过。而且我也是《头号玩家》这个电影的粉丝,看了好几遍,我是觉得非常震撼。
Vision Pro 的定价太贵,它其实用的是特斯拉的策略。
特斯拉的第一款车是非常贵的。我们能够看到马斯克的选择:即我要做一款智能汽车,而不是一款新能源车。那这辆车的定位到底是给年轻人的第一辆车,还是给有钱人的第三辆车?
我们来看马斯克的选择。其实他的第一台特斯拉是一辆跑车,包括它的百米四秒加速、推背感等等,会让用户很 high,愿意付这个钱,它的定位就是有钱人的第三辆车。接着他用这一群最挑剔的人帮他打磨用户体验。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效率的进步,包括像这种智能设备的体验,其实它一定是成瘾性的。我几个朋友都是开了特斯拉以后,就开不了其他的车了,即便是特斯拉有各种被大家吐槽的毛病,也开不回去了。在用户成瘾之后,特斯拉的产品价格再往下降。
所以我相信苹果一定也是这样的。苹果在粉丝的心中的信任度很高,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人,肯定是要购买 Vision Pro 的。实际上,他其实要的就是最挑剔的、用户体验最多的这群人帮他打磨体验。但接下来电子产品它的规律一定是价格向下的,成本一定会降下来,再慢慢往外推广。
我们过去看过那么多代的 VR 产品,包括国内的这些,比如冯鑫做的暴风 VR,谁都不敢说我要做一个 2 万块的 VR。
刘江:回到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我们不太敢去创造这种比较突破性的东西,这也和刚才讲到的中国 96 年的情况相关。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相对比较穷或者比较低的位置开始发展的,能力是慢慢往上爬的。
虽然这几十年我们的进展确实很大,但 ChatGPT 出来以后,大家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做出来”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心里觉得中国也应该有这种能力。
梁宁:我们整体企业的能力是低端规模能力。
这些年其实做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也非常多,但就像刚才所说的,ChatGPT 首先是先搭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计算集群,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先干了个工程创新。
我们中国目前最大的是 4000片,那就是 4000 片和 1 万片的区别,就是 40 层楼和 100 层楼的区别,那根本就是两种技术能力。所有的设计、地基、材料、交互都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刘江:还是需要有比较强信念感的人来做这些。
Ilya 其实非常强调,我们还是有信念;Sam 则比较强调要把这种比较创新的、严谨的科研文化,和你刚才强调的工程文化、落地的文化,两者能融合在一起。
我们都知道真正搞创新的是科学家,或者说有很多想法的人,但是他们其实不太考虑最后怎么能把想法落地,能大规模地实现。
梁宁:一个是这个,还有一点是我们的企业家。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咱们国内的人,我们都想的是“我如何降本增效”。
所以大家都想的是,你用 1 万片,我能不能用 9000 片?你用 9000 片,那我能不能用 8000 片?你用大模型、大数据,我能不能用小数据加洞察来完成这件事儿?我们的一贯逻辑就是:我能不能降低成本。
降低成本,这是我们的创新。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创新范式就是对方实现突破,我们来想办法降本增效。
刘江: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个既定的圈子里头来思考。
梁宁:对,是的,我们一定要跳出去。所以当我看到苹果的 Vision Pro 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
之前我和一个朋友讨论过为什么苹果没有做电视。因为实际上用户消费的并不是电视,不是屏幕,而是数据,信息,然后是图像。所以苹果提供了这个后,他就停在这了,他就没有再去做那块屏幕。但是小米就做了电视,华为也做了电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苹果不做电视?
刚才其实刘江老师说了一个观点,我也非常认同,他怀疑苹果觉得电视的利润率无法达到苹果的要求,所以苹果就不做。
生态位决定了企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梁宁:但是换句话来讲,是苹果它有这份傲气,就是骄傲:我只挣最难的钱,我让你有这种跨越式的体验,但用户必须得为这种跨越式的体验付超多的钱,最终我要拿掉这个行业 90% 的钱。
比如说耳机,咱们中国华强北占了全世界的耳机份额很大一部分,但最后全世界耳机利润的 90% 被苹果拿走。这是一个选择:企业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活着,要在什么样的生态位上活着,这就会导致你的整个企业的能力建设在哪儿。但是也要绷住一股劲儿,就是这个(市场)我就是不去吃。
比如,苹果以它的身位发布一款电视,那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一堆用户来买。但是他就绷着一股劲,我不做这个产品。
刘江:苹果甚至可以学小米一样,什么都可以搞一个“苹果牌”,那它的营收会很高。这就是战略问题,苹果他从自己的各方面去判断,有很多利润低的不值得去做。
梁宁:因为如果像这样去做的话,会让他整个企业的能力模型变形。
因为苹果保持着苹果的骄傲,永远是为用户提供这种跨越式的体验,所以才会有忠诚的果粉,才会有工程师攻克这些难关的骄傲,才有他的生态位。
换言之就是这些容易的食儿,你们去吃,我不捡,地上的东西我不捡。
刘江:梁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做这个判断,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有一个底层资源的限制。
我观察其实在很多比较高精尖的这个事情上,人才其实是稀缺的。所以我现在反过来也觉得,就是真正要做特别漂亮的事儿,可能人才也是不太够的。
梁宁: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今天的主题 ChatGPT。 实际上什么叫人才,人才就是一个知识模型。寒窗苦读学的是什么,就是学个知识模型。读完书出来以后人赚钱就是变现,劳动力变现就是蓝领,知识变现就是白领。
所以刚才你说到的知识不够,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已经把知识贡献给了 GPT,那么可能未来这些企业去聚集和使用知识的方法也会发生变化。但回过头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做不出来?我觉得这和我们整个民族过去几十年所培养的环境有关,就是“不敢”。(我们)就是做一些相对低端的产业,挣地上的钱的。如果不把自己逼到一个井底,比如说我只挣难赚的钱,地上的钱不挣,那我们整个能力模型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一家企业,你看到的是产品,然后是产品体验,背后其实是这个企业的团队的能力。我们会发现一个企业和它的业务是相互塑造的,你做这个业务,然后业务也反向塑造你的团队,你吸引的也是同种类型的人。
一挑战高难度的事儿,大家就不愿意干:我明明可以获得安稳,我每天一低头就能吃草。那我为什么要万里奔袭,八年磨一剑,去为了这个东西努力创新呢?
-
兆易创新荣获2025“中国芯”优秀技术创新产品奖2025-11-19 451
-
苹果混合现实头戴设备Vision Pro将启动预售2024-06-13 1190
-
OpenAI推出Vision Pro版ChatGPT2024-02-06 1352
-
登临科技创新通用GPU荣获“中国芯”优秀技术创新产品荣誉2023-09-22 2515
-
Vision Pro商标遭华为抢注!苹果或更新名2023-08-18 3039
-
苹果vision pro2023-06-12 1887
-
好了,我们来好好聊聊Vision Pro这东西吧!2023-06-07 1070
-
科技大厂竞逐AIGC,中国的ChatGPT在哪?2023-03-03 2210
-
芯原NPU IP荣获“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奖2022-11-29 2455
-
CES可穿戴创新产品超长电池续航揭秘2019-07-02 1990
-
“第五大发明”智能制造科技创新产品对接会2016-05-18 4348
-
杨海涛:产品如何创新PPT—中国硬件创新大赛上海培训会2015-06-11 8022
-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国家一级期刊约稿2009-06-03 1388
全部0条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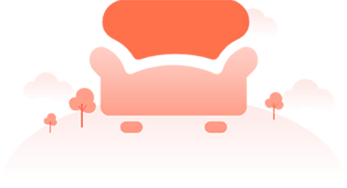
快来发表一下你的评论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