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中国创新中心领导人王玮:点燃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篝火”
电子说
描述
数字化转型话题由来已久。而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企业更面临如何通过内生研发或外部引进完成“数字化转型 2.0”的新挑战,“Beacon”专栏应运而生。本专栏从技术如何撬动变革的角度,对话这一领域的实践者、思想者和服务者,沉淀经验,启发思想,推动改变。首次“Beacon”对话由《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文版副出版人、DeepTech 深科技联合创始人陈序主持,受访者为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麦肯锡中国创新中心(CIH)领导人王玮。
北京 4 月一个早晨,金茂威斯汀酒店的行政酒廊。这里可以看到沿着东三环向南伸展的 CBD 区域,一直到高耸在薄雾里微微闪光的中国尊。从 1985 年开始,麦肯锡就进入了大中华市场提供咨询服务,伴随中国经济起飞,见证中国互联网弯道超车……如今,麦肯锡又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中找到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对话开始前五分钟,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王玮拖着一个万向轮的登机行李箱匆匆赶到。我们都要了咖啡,王玮加点了煎蛋作为工作日的早餐。
图|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王玮
以下为本次对话内容:
陈:麦肯锡如何想到创立 CIH(China Innovation Hub,中国创新中心)这样一个试验性的机制,又如何着手实施?
王:其实,早在成立 CIH 之前,我们的数字化相关业务已经有很多发展,包括 Digital Mckinsey、McKinsey Analytics 等等。但从客户 CEO 的需求角度来看,所有跟数字化创新相关的服务最好有一个整体的蓝图和路线图。
再者,从执行角度来讲,数字化转型肯定不是光做一个战略规划就能产生效果,一定要和迭代共创。
最后,执行数字化战略还需要特殊的人才组织结构。除有数字化经验的战略顾问外,还得有数字化实施的专才,如架构、设计、敏捷、产品经理。
如上所述,既然客户的需求同时包括整体战略加上执行落地,我们为此搭建的人才组织结构就需要把这些不同的点线面集中起来,集成在一个机制中,帮客户一揽子解决数字化创新相关的问题。这就是现在的 CIH。
陈:发展到今天,CIH 业务在麦肯锡中国的整体业务中是一个什么地位?
王:一个百分比数字可以简洁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数字化业务已经占到整体业务的30%。
陈: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把技术专才引入到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强势的咨询机构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王:是的,会有挑战。数字化实施的专才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他可能是在互联网领域创过业、经验丰富的产品负责人,可能是技术架构师,也可能是产品、用户界面或用户体验的设计师,当然也可能是数据工程师。这些人才无法根据麦肯锡传统的岗位描述招来再培养或包装一下获得。另外,专才要有特定的培养机制。和传统的咨询顾问放在一起去评价的话,会发现这些人有专长,但也欠缺一些咨询服务的技能。所以,从招聘到培养,我们都得另起炉灶。
我自己是数字麦肯锡人才委员会亚洲区的负责人、全球董事合伙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很了解麦肯锡是在多个维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职业路径要定义清楚。麦肯锡一个咨询顾问(consultant)要成长为合伙人(partner),按传统标准必须是全才。这个人具备的客户服务、客户咨询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团队协作和领导团队的能力也必不可少,还必须在某个知识领域有专长。然而,用一个面面俱到的模子压在一个专才身上,这不公平。一个能力很强的数据工程师不一定能在客户面前讲好方案;有创意的设计师可能做不好一版逻辑清晰的 PPT。虽然他们同样在为所有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但不一定能完美服务客户团队中的所有人。数据科学家可以服务客户团队中的数据科学家,设计师可以服务客户团队中的设计师。专才只需要服务好客户团队中相关专业领域的人,不必强求他是全才,或者要有领导力。因此,对专才的成长要求就不能像对咨询顾问,不能只追求成长速度,而要给予充分的耐心和理解,根据他的路径,帮助他用自己的节奏往前走。我们管这叫 grow or go,就是你只要能够成长,我不在乎你什么速度,你只要服务好客户,也不在乎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成长机制中,专才也能选拔为合伙人,我们叫专家合伙人(expert partner),或大师级专家(master expert)。
其次,项目组队的方法。在一个具体项目上,只把专才打包在一起去服务客户是有问题的。麦肯锡要服务于客户的战略,和 CEO 或 COO 打交道,所以团队必须有连接企业所有业务价值的能力。项目团队的领导,如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应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咨询专家,团队里也需要有专才和全才的组合。
另外,要有过程管理。要和专才们约法三章,不能说这个活交给他就不管了,三个星期以后再来看结果。管理上必须先有计划,有节点目标。团队要有主动的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客户最关键的战略问题能够得到最大重视,而技术部分的执行也能够到位。
陈:麦肯锡中国用多少时间储备了多少技术专才,包括达到大师(master)这样高级别专家水平的?
王:现在我们已经有 120 名这样的专才。麦肯锡中国有一千多名员工,在中国区有 500 多名咨询顾问。我现在负责亚洲部分的数字麦肯锡副董事合伙人评定,副董事合伙人级别在我们内部就是合伙人预备队了。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1/3 的副董事合伙人是全才;1/3 是专家副董事,有非常聚焦的专业或行业领域;还有 1/3 是资深专家,就是专才。这最后三分之一的专才可能不会在客户服务中扮演领导的角色,但会在技术服务中扮演领导的角色。
反观大概六七年前,我刚开始做副董事合伙人评定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八二开,80% 是全才,20% 是专家副董事。
陈:传统企业数字转型如何控制风险和成本是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转型本身是否成功,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客户是怎么来判断的?
王:以前评价我们的工作成效比较难。因为原来是做一个战略规划,如果效果不好,很难判断应该归咎于方案本身还是执行。
现在比较简单,我们的数字化项目一般是以教练加运动员的方式来做,时间周期至少在六个月以上。从设计最简可行产品(MVP,Minimun Viable Product)到实施,再把之后的路线图设计好,中间每个关键节点都要很清晰。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培训客户的团队,引进外部的实施合作伙伴。
这样的项目会相对容易评价。比如针对业务定位的问题,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设计的 MVP 目标是不是实现了,MVP 是不是得到了市场接受。另外,我们会帮助客户把相关团队建设起来,即使我们离开后,也要保证它能井然有序地运转。业务负责人到位,不同决策人员到位,各自知道怎么工作,这样才是成品。相反,如果我们离开后就一地鸡毛,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了。
陈: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上会经历蛮长的一个时间周期,外部的技术发展迭代却非常快,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也是千变万化。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市场环境和技术创新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会不会需要调整原来的整个方案?
王:完全有可能。不过,我不觉得外部技术创新会是造成方案调整的一个主要原因。技术发展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不是说突然谁发明一个新标准,我们就得转方向。这一类突发情况出现的概率并不高。我觉得调整更可能是因为我们推进项目需要跟时间赛跑。为了最高效率地做出 MVP,初期方案用的技术架构,和长期可规模化的技术架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以前学生时代去野营,对点篝火的过程印象非常深刻。要点燃篝火,一上来要先把木头交叉架起来,等到火势起来后把木头全拿走,再架成井字形。我问指导员为什么要架两遍。他说井字形的架法火不容易点着,得先架一个结构让火起来;但容易点火的结构其实烧不了多少木头,所以火着了之后必须再换个结构。
我现在也是这么做:MVP 要找一个半现成的方案,先把业务跑通,业务通了之后再重构技术架构,更加规模化,更加考虑固化。根据项目进展换技术架构,比一上来用一个不适合的技术方案,成本反而低。
陈:我发现经过长时间培育,随着环境变化,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但很多传统企业,尤其大企业,对数字化转型仍心存疑虑。很多企业决策者对转型投入所能够带来的回报并不肯定。麦肯锡对此怎么看?
王: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我觉得关键取决于“一把手”的远见。
我见过几种“一把手”。第一种是“平衡型风格”。他认为数字化是重要,内部对团队会讲,外面对媒体会讲,但他给自己的任务是继续抓好原来的主营业务。结果,就会把数字化转型项目交给一个副总来负责。这时问题就来了。这个负责的副总当然会有自己一整套想法,但这个想法跟同僚往往并不一致,且很难达成一致。当一个副总不能说服别的副总,项目就会原地打转,一转半年都没进展。这时 CEO 再不出手,转型就可能黄。
第二种“一把手”更有挑战性,可以叫“思考型风格”。他会在论证上花很多时间,公司上下反复讨论。讨论本身很积极很认真,但他不会在组织层面上做调整,团队里也没有人会承担一个 KPI 把事做出来。
第三种“一把手”是我最看好的,就是“偏执进取型风格”。这种风格的领导者很多是民营企业家,主营业务成功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明天,非常前瞻。一方面他们全球跑,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创新企业,不管是消费品、零售还是互联网,和自己业务相关不相关的都看。另一方面他们不断观察自己的消费者,有一个董事长甚至天天跑店,天天在店里呆着,观察自己的创新有什么反馈,还亲自带队迭代数字化产品。这样的“一把手”带队搞创新,谁敢不跟?可见,进取而偏执的企业家才能做出领先行业的创新,也才能真正顶住压力。
陈:能否举例讲讲你在服务过程中碰到过的第三种“一把手”?
王:我最近正好在帮助一位客户构建一个市场化数字平台。从我们双方开始谈,到确定麦肯锡来做这个事,只用了五天:第一天双方谈清楚需求,第四天我提交方案,第五天再碰面谈定价格。这就是典型的“一把手”重视、主动推进达到的成效。我们交流的那一天,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全程跟我们团队谈,然后就是最后一天来确认方案。整个过程快速高效但不草率,让我也很有感触。
陈:在中国,政府在市场制度安排上很重要,有时是最重要的。麦肯锡有没有观察到政府在数字化转型的引领会对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我们和企业在做一个数字化平台,政府非常支持。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很前瞻,非常清楚要用一个正确的机制来推进数字化转型,也充分认识到如果全部由政府设计、政府牵头、国企带队,这样做可能会有弊端。很多地方政府希望让更有市场化运作能力的企业来做主体,自己来提供政策和资源整合方面的支持,让企业走得更远。有这样的支持,企业也会更积极。
陈:有的企业会采取“内生创业”的模式做数字化转型,就是先不动大的组织架构,而在内部孵化一些项目,让它们自己跑。对这样的模式,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效率低,不如顶层设计、整体去做来得彻底;另一派则认为这是好的策略,可以自下而上产生一些创新动力,然后再去推动整个企业的变化。你怎么看?
王:传统企业肯定有一个造血的主营业务,随便去动主营业务,其实不太现实。组织有惯性,经营有规律,所以从零开始就做整体转型很难;但如果让每个业务部门去开个小作坊做创新,然后各讲各的故事,也不太靠谱。因此,必须既有自上而下的判断,也有自下而上的试验,两者要有机结合。
陈:近几年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数字化转型市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也会深刻影响咨询业。最近很多国际机场出现了咨询公司投放的大量数字化转型业务广告,也可以从侧面看出行业竞争格局与趋势变化的端倪。麦肯锡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王:我们内部做过一个市场研究,也觉得咨询行业会发生很大变化。原来分成战略咨询、IT 咨询、IT 实施、数字化实施这样的一个个子市场,现在它们的边界在模糊。边界模糊意味着一个更大的市场。这是件好事,因为一个企业购买数字化咨询的预算肯定大过单纯战略咨询的预算。
需要强调的是,麦肯锡的服务不是普通的、无差别的商业产品,而是定制化的。麦肯锡拥有全球及专注于区域的专家资源网络,来帮助解决最为紧迫的商业和经济问题。我们每年对知识创造和积累的投入超过 6 亿美元。通过分享这些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形成的知识积累,我们有效地传递了麦肯锡的品牌价值。
陈:如果把视点从咨询服务扩展到整个科技服务市场,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科技服务业还缺少一些基本的支撑。例如,在美国已经发展成熟的高校科技成果商业转化服务、硬科技风险投资服务、科技媒体服务和专业咨询服务,这些方面,中国市场的供给仍明显不足。于是,就有很多具有技术基因的公司进入这个市场,来分一杯羹。以你领导 CIH 的经验,怎么看这些新的参与者?
王:科技服务尽管有它的科技硬核,但我认为它背后仍然是传统的 B2B 客户服务。麦肯锡多年来总结的 B2B 客户服务经验,始终适用于这个市场,也适用于具有技术基因的这些公司。
这些技术上强的公司,往往一两个创始人在某个领域的数字化技术能力特别强。但它缺少原生的服务基因。这样的公司要真正服务好客户,或者在服务过一两个客户之后进一步成体系地服务更大规模的客户群,还要克服很多困难。
比如,科技服务公司不能仅仅通过和客户的技术部门单点接触就做好完整的服务,因为技术部门搞不定业务部门。如果不能撬动客户整个组织系统的转型机制,技术方案到位以后的实施与应用还是会举步维艰。
陈:最后,如果用一个词来向你未来的客户 CEO 描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点,你会用哪个词?
王:我觉得是两个词:第一是结果导向,第二是迭代。这两个是最核心的。数字化战略不可能一版就到位,需要领导者的决心,需要设计和实施者的探索,需要不断迭代。
-
喜讯!华秋荣获2023中国产业数字化百强榜企业2023-12-04 1203
-
SNP应邀参加2023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峰会暨赛意用户大会2023-11-09 991
-
工业4.0上时代,数字化转型的五大优势2022-11-21 1502
-
亚马逊云科技发布中国企业上云出海趋势 全球优势赋能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思考 本地化运营”2022-04-26 2154
-
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分享2021-08-19 13798
-
数字化转型系列主题:究竟有哪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功了?精选资料分享2021-07-12 1990
-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存在诸多矛盾2021-04-19 4832
-
强韧、创新、突破 2020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2020-12-17 2515
-
埃森哲研究:11%中国企业数字转型出色2020-10-15 2604
-
66%中国企业没有看到数字化投资在促进收入增长的作用2020-09-16 1717
-
"新基建时代",中小企业该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2020-05-19 3396
-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没有必要?2020-05-18 2797
-
谋求数字化转型,中国 IT基础设施“跨越式演进”2019-04-07 3457
-
聚焦转型创新,中琛源数字经济前沿论坛即将开幕2017-12-22 2922
全部0条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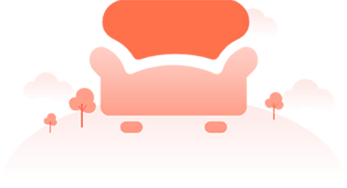
快来发表一下你的评论吧 !

